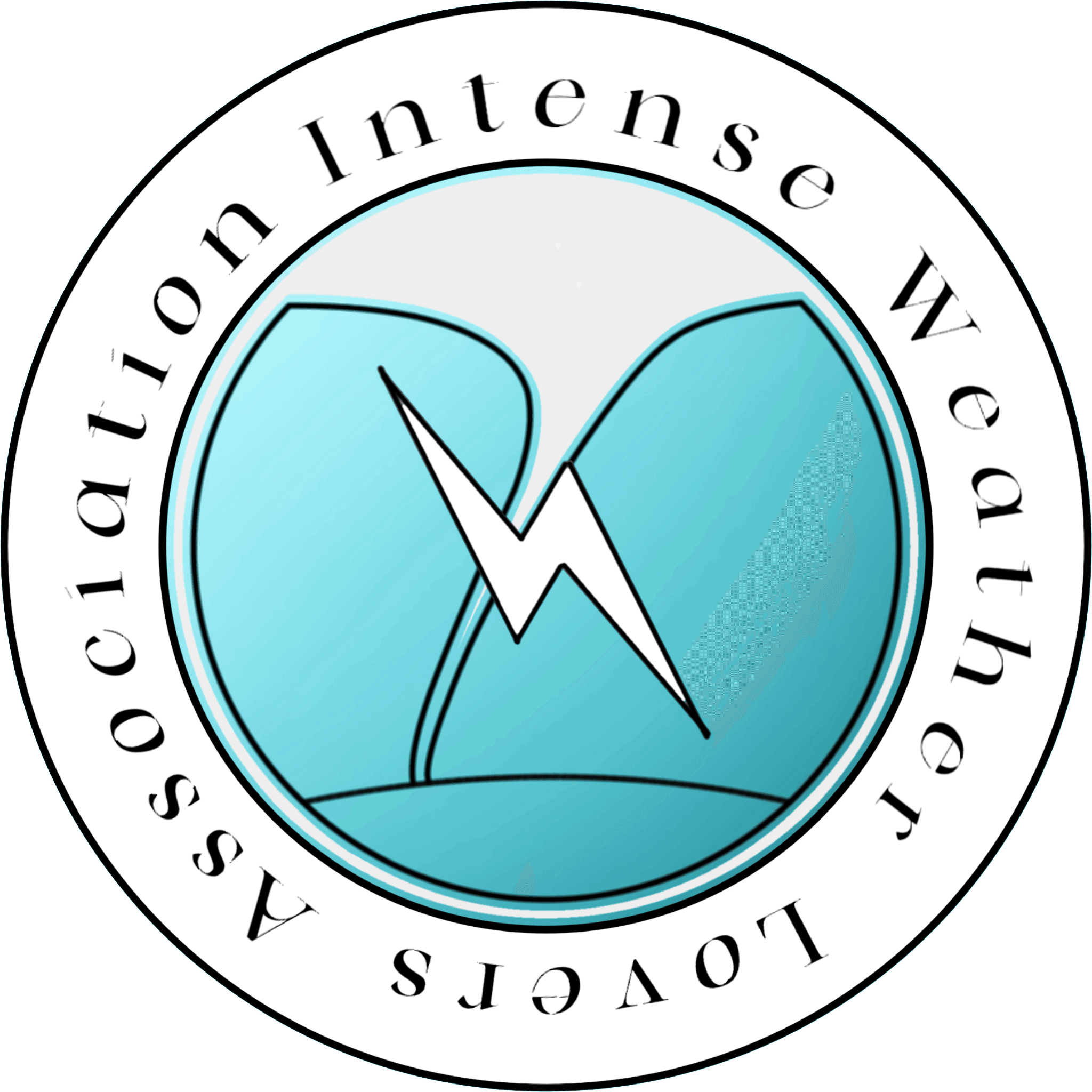为什么要“众说风云”?
气象爱好者,这样一个小众、边缘、独特,甚至有些奇怪的群体,在家人警告安全非儿戏时,他们望着闪电入迷;在路人埋怨天公不作美时,他们冲进狂风暴雨;在众人祈求风调雨顺时,他们却因为破纪录的数据、历史级的影像兴奋不已……在或许不算少数的人看来,“气象”与“爱好”无论如何也沾不上边,耳熟能详的“人定胜天”口号,加之气象与军事千丝万缕的联系,让大家觉得:变幻莫测的天气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凶猛“敌人”之一;那“气象爱好者”呢?是叛徒?还是帮凶?甚至是某个更险恶的黑暗势力安插的奸细?或许,事实并非如此。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上都有哪些“气象人”:
中国历史上,有编写《相雨书》的黄子发,有《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更有我们熟知的中国现代气象奠基人竺可桢先生。
中国以外,有传奇人物亚里士多德,科学先驱笛卡尔,“旋风先生”藤田哲也博士……
我在这里使用了更加被广泛接受的“气象人”一词,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或是受命于王室,或是在其它学科探索过程中的意外之得,并不完全是出于爱好。但近代以来越来越多有鲜活资料的可考历史中,各领域萌芽于爱好的伟大学者均数不胜数,且在数量占比、研究成果等指标上呈现出绝对优势。
如果要问,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气象爱好者是谁?我想,是早在文明诞生前,我们共同祖先中的一位,在风吹雨打,电闪雷鸣的天气中,用被恐惧晕染却又充满好奇的目光,首次打量天空。这之前,天空是魔鬼的大门,是灾厄的源泉,但从这一瞥开始,一股气流、一团水汽、一朵乌云、一滴雨水,天空有了生命。
在驯服狗之前,人类对狼群怀着深深的恐惧,在仰望星空之前,人类对黑夜怀着深深的恐惧。观察、记录、欣赏、共鸣,而非对抗,是人类与自然实现真正和谐相处的必由之路。
气象爱好者从不抱怨天不作美,因为我们知道风云变幻自有规律;气象爱好者从不奢求风调雨顺,因为我们知道气象万千才是生活。
正因风云变幻无时无刻不在深刻影响着芸芸众生,我们才需要让气象从神秘的高阁中解放出来,才需要众说风云。
为什么是“众说风云”?
为什么我要做《众说风云》呢,或许是私心作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满足一下自己爱写东西又爱收集汇总各种资料的小癖好;或许,这可以满足我不想让更多新人走和我相同的弯路,让圈子里出现更多快速成长的成员的小愿望。
我自己的“入坑”经历,不说一波三折,也是如蜗牛爬坡般缓慢且吃力。
幼年时的我住在广州,那是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也是一座风狂雨骤的城市。家住高层,卧室有一扇飘窗,从还没有记忆时开始,我就喜欢躺在飘窗上,望着夜空中时不时划过的闪电,充满神往。再大一点,我开始把铁钉、铁丝等绑在棍子上制作“避雷针”,把它悄悄探出去,渴望着与闪电“亲密接触”(现在想想还好用的棍子是玻璃纤维而不是碳素(-。-;)后来随家庭事业变更迁居河南,这里的天气索然无味了许多,但科教、记录频道与求索记录(Discovery)频道上的《追风部队》纪录片,《龙卷风》电影等又上了我的必看榜单,小游戏《云和绵羊》陪着我人生中使用的前几部智能手机走到了它们使命的终点,《爱丽丝梦游仙境》中龙卷风把房子和人一起搬走的能力令我深深折服,《神奇校车》中深邃的台风眼更是让我神往无比。夏季风云突变的午后,我照常望向天空,按照自己从游戏中得来的粗略的理解,期盼着有两朵乌云能撞向一起,催生出神秘的龙卷风,小学美术课上,我用稚嫩的线条幻想着利用龙卷风的吸力处理垃圾……我在校友群里定时定点“拍照打卡”记录天气,甚至被同学打趣:“你是天气预报员啊?”这时的我,莫谈什么理论知识,甚至连气象学/大气科学这一学科的存在都不知情。
但一切都在2018年的8月被改变了,2018年第18号台风“摩羯”罕见地深入内陆,环流中心跨越河南省界,直奔我的住地-漯河而来。电视台开始密集播报、手机频繁收到预警信息,在我单纯的世界观里,似乎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即将到来……终于,8月18日放学后,风云突变,风催动的雨滴仿佛一排排雨墙朝人们垮塌下来,成排的自行车倒下,家长被允许进入校园接送学生,我和同学们困在教学楼的屋檐下,淋湿了头发,衣服,甚至书包,直到天色渐暗,才成功回了家。终于安顿下来的我发现自己在发抖,并惊觉这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兴奋。
这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彻夜翻着手机,“百度台风吧”“台风路径”“讨论台风:201818温比亚”……六年级的我,隔着网线,上了由无数前辈共同贡献的第一堂气象课。
那之后,我学习了基本的台风知识,并努力想要融入大家的讨论,可是缺乏科学逻辑的我在前辈们眼中活脱脱是一只“皮鸭”,终于,2019年1月24日,我被踢出了“爱台风”QQ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决定组建自己的气象群,在把朋友列表里与气象有关或无关的十几个人拉进群后,我还恬不知耻地用自己最喜欢的纪录片命名了这个群聊——追风部队(StormChasers)。
2019年7月3日,辽宁省开原市发生EF4级龙卷风,通天的风柱,滚滚的红尘,扭转了无数钢筋铁骨,也扭转了我的气象之路。当时,在我简陋的认知里,“超级单体”与“龙卷风”是几乎独属于美国的天气现象,但它却在我自己的祖国现身了。羞愧感排山倒海而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曾引以为豪的那点儿知识是多么可笑,当天夜里,我按照网友的推荐下单了《天气学原理和方法》《中尺度气象学》,晦涩难懂的公式、无中生有的名词,书本翻了三五遍,笔记画了一大堆,我却自觉没有丝毫长进。一次偶然,我翻到了吧友“风抚幽夜”发布的强对流过程分析,长短波、深浅槽、T-lnp图、CAPE、钩状回波等不知所以的名词突然具象化了起来,我开始理解大气的垂直分层、能量的输送与转换、不同尺度天气系统的差异……
学到这里的我,感觉自己“又懂了”,我从台风论坛等各种平台的科普文章中挑挑捡捡,在各种东拼西凑和杜撰之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教程”《超级单体-HP与LP》,紧接着是《追风新手如何使用雷达产品辨别超级单体》,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作品居然受到了吧友的欢迎,论坛激烈天气板块的前辈还邀请我发布到台风论坛,更令我狂喜的是,我收到了一条做梦都不敢想的好友申请。
“风抚幽夜 请求添加你为好友”
我激动了一天一夜,才颤抖着手确认了申请信息。
“你写的文章我们看了,挺不错的,但是你文中提到的……”
或许是为了减少对更多新人的误导,或许只是想拯救一下我这个写东西一半靠搜索一半靠脑补的“皮鸭”,论坛激烈天气板块的几位元老找到了我,教我一步步修改帖子内容,以至于最后我删掉了所有全部内容重新来过(现在原贴内仍可见当时的修改痕迹),总之,或许是幸运使然,我阴差阳错地结识了气象路上最早的几位老师,而这几位老师真正改变了我至今的人生。
2019年10月2日,“追风部队”更名为“激烈天气爱好者协会”,至此,我方才真正走进气象世界。
回望自己的学习过程,再结合身边众多同好的成长经历来看,我认为中文互联网在气象领域、尤其是强天气领域的入门通识资源是严重缺失的,虽然有大量前辈贡献的优秀文献与研究成果,但是缺乏一个通俗化、流程化的学习指引,导致大量新人的入门过程极度吃力,甚至催生了一些偏激、逻辑混乱的“爱好者“,对气象事业与气象爱好者群体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激烈天气爱好者协会建立并基本稳定运行之后,我和诸多朋友们一直坚持收集、汇总、整理气象方面尤其是强天气领域的资源与资料,至今六年有余,资源总量业已达可观。
最近两三年来,我有幸见证了IDA、浓积云、多单体、muifa等00后同辈尤其是07后晚辈的飞速成长,他们迅速达到了断代级的领先。同时我也深感自己的落后,所以我想,趁着自己没有彻底隐入尘烟之前,为自己热爱的强天气领域留下一些痕迹,写一个入门通识教程。
如能够帮助更多人发掘爱好,尽早走出弯路,并欣赏这些自然造物的美,这将是我在这条求索之路上的卓越迈进。
为什么能“众说风云”?
新世纪伊始,互联网的全面普及,让气象爱好者首次联系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在中国(大陆),2002年,“台风论坛”初创,如满天星辰般散落各地的气象爱好者终于有了一个认识同好、共同交流学习的平台(如今大家所熟知的“中国气象爱好者”与台风论坛论坛亦同宗同源)。随后,2004年百度“台风吧”建立,2012年百度“飑线吧”建立,“冷空气吧”、“爱台风”“上海追风团队”“联合气象研究组”“云鸥气象”……从整个气象爱好者群体到各个领域的分支,国内的气爱文化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
这是可喜的进步,但弱中心化状态下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局部失序:有“气象爱好者”未经允许进入、接触气象探测设施,向雨量桶倒水,甚至在百叶箱下放火;互联网上,“气象爱好者”与气象官方媒体的攻讦与骂战层出不穷。气象部门对气象爱好者的提防与排斥广泛存在,气象数据的公开程度愈发降低,旧”台风论坛“毫无征兆的突然关停更是对我们造成了沉重打击。气爱群体与气象部门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
但气象爱好者对我国气象事业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极个别人让群体蒙羞的恶劣行为。气象爱好者向身边人的言传身教,在互联网上发布的科普作品,对公众防灾意识与科学素养有显著正面影响;在国内受到极大欢迎的雷达基数据绘图工具库pyCINRAD是由一位来自四川的气象爱好者在留美深造期间开发的(巧合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的天气雷达综合分析程序GR2系列也是由一位曾为微软工作的气象爱好者开发)。更是有大量气象爱好者选择攻读大气科学专业,在兴趣与责任感的共同驱使下,他们将成为未来我国气象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中国气象爱好者”等自媒体的出圈爆火、资深气象爱好者越来越多地受邀登上公众舞台、气象爱好者与佛山市龙卷风研究中心在龙卷个例收集工作中的广泛合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